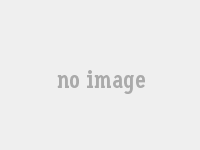吉林省前郭县一起看似普通的鱼塘赔偿纠纷,经由刑事程序的异化处理,演变为被告人贾秀华、武国光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案卷中,一份长达数十页的上诉状及证据材料,字字泣血,控诉着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环环相扣的程序违法与实体不公。这起案件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当公权力偏离法治轨道,司法公正如何在程序异化与事实切割的双重绞杀下黯然失色。
一、程序正义的崩塌:司法沦为打击报复的工具
本案司法程序的启动与推进,弥漫着浓厚的“定向打击”气息,程序法沦为可任意揉捏的工具。
非法立案的“罗生门”:贾秀华因长期上访举报地方官员涉嫌贪腐(包括焦文国等人侵吞征地补偿款、掩埋有毒泥浆污染环境),其举报对象涉嫌犯罪的线索,竟离奇地“转化”为针对举报人本人启动诈骗罪侦查的“案件来源”。更令人费解的是,首次初查已认定“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却又蹊跷地再度立案。这种举报人与被举报人身份的反转,程序上的反复无常,缺乏合理合法的解释,指向了利用刑事手段压制正当举报的恶劣逻辑。
程序规则的系统性失效:重审过程中,面对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明确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一审法院竟“置之不理”,粗暴剥夺了被告方的核心诉讼权利。法律要求关键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法院却对证人拒不出庭的行为不施加任何制裁,甚至不将关键证人证言纳入补充调查范围,导致庭审质证形同虚设。更公然践踏法律的是,在两次补充侦查的法定上限之外,违法允许第三次补充侦查,且对补侦获取的证据,未经法定庭审举证、质证程序便直接作为定案依据。这些行为非偶然疏失,而是系统性剥夺辩方权利、架空正当程序的集中体现。
“以刑止访”的赤裸意图:案件之所以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反复退补、延长审限、判处重刑,核心目的就是“配合‘上级’意图打击报复”,“意图通过超期羁押和判刑投监使上诉人无法上访”。司法机关本应是权利的最后屏障,在此案中却沦为压制公民合法申诉权的帮凶,程序正义的基石荡然无存。
二、实体认定的扭曲:法律事实被选择性切割
一审判决在案件核心事实的认定上,采取了精妙的“切割术”,刻意回避对上诉人有利的关键事实,仅撷取碎片化信息拼凑“罪证”。
故意割裂的经营历史:判决书对贾秀华自2011年起即实际经营管理案涉泄水渠(投放鱼苗、持续管理)并形成养殖规模、产生收益的客观事实(卷宗有充分证据证实)完全回避。只聚焦于2019年补缴承包费后的时段,人为制造“无合法经营权”的假象。这种割裂无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普遍存在的“事实先行,手续后补”的客观现实。
“三资清查”政策的司法失明: 2019年,省、市、县三级推动农村“三资”(资金、资产、资源)清查,核心目标正是将农民实际开垦经营的荒山、荒地、水面等资源“规范、登记造册,纳入集体台账,确认权属”。贾秀华正是在此背景下,经乡、村两级组织确认权属后补缴承包费,乡、村据此决定将鱼塘全部赔偿款直接支付给她(而非截留大部分仅付成本,有村委会纪要为证)。这一具有确权效力的关键行政确认行为及其背景政策,判决书竟“一概没有认定”。判决仅以“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为由否定其经营权,粗暴违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关于“承包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及承认事实承包关系的精神,也否定了“三资清查”这一地方治理实践的法律意义。
赔偿协商本质的刻意歪曲: 判决书的核心逻辑建立在“虚开票据导致高额赔偿=诈骗”之上。然而,评估报告本身清晰表明:评估机构因损害现场已破坏、投入产出无法精确查清,明确放弃依据任何票据(无论真假),转而采用吉林省粗养模式的理论参考值。报告特别强调该值“不作为确定的赔偿额,仅供协商参考”。实际赔偿额是四家涉事公司、上诉人、乡村干部多次现场踏勘后协商确定。虚开票据行为(如存在)与最终赔偿额的确定之间,缺乏刑法上的直接、必然因果关系。判决书对此核心事实选择性失明,强行嫁接因果关系。
双重评估标准的荒诞逻辑:侦查初期曾委托评估损失为73,860元。一审判决在认定诈骗数额时,明知上诉人存在实际损失(承认73,860元评估的合理性),却拒绝将这部分应从总赔偿额中扣除,导致逻辑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有真实损失需赔,另一方面又将包含真实损失在内的协商总赔偿款全数认定为诈骗所得。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判决为入罪而强行拼凑数额的窘境。
三、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法理崩坏
一审判决对诈骗罪的认定,在法理层面存在根本性缺陷,完全不符合该罪名的法定构成要件。
主体资格非虚构:贾秀华作为多年实际经营并因“三资清查”获得乡、村两级确认的经营权人,是受损鱼塘的合法利害关系人。即便其经营权合法性存在争议(判决错误认定),侵权赔偿的直接义务对象也是作为所有权人的村集体。村委会明确决定将受偿权转交实际经营者贾秀华,这属于民法上有效的权利处分(意思自治)。司法机关无权以刑事手段否定这一民事安排的效力,更无权剥夺上诉人作为实际受损方获得赔偿的民事主体资格。
非法占有目的缺失:上诉人在鱼塘受损、现场无法复原、赔偿标准难定的复杂情况下,其与各方沟通协商(包括提供票据等行为),核心目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损失难量化困境中,争取相对合理的赔偿以弥补真实损失,而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其行为具有民事权利主张的正当性基础。
欺诈行为与财产交付因果断裂:诈骗罪要求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须指向关键事实(如主体身份、损害发生、财产权属)。本案中,四公司清楚知晓赔偿对象是实际经营该鱼塘的村民(贾秀华),知晓损害系其施工所致,知晓赔偿款的性质。评估采用的是定额模式而非票据金额,赔偿额是协商结果。四公司支付赔偿款是基于其侵权责任及协商结果,并非基于对虚开票据所虚构的“巨额损失”的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支付后也“至今没有异议”。核心事实无虚构,处分财产非基于错误认识,诈骗罪的核心链条已然断裂。
被害人错位与退赔荒谬:四家公司是侵权责任人,依法负有赔偿义务。其支付的赔偿款(无论给谁)是履行法定义务。即便支付对象有误,其财产损失也源于自身过错(侵权)及可能的内部管理责任,而非上诉人的诈骗行为。一审判决将侵权责任人认定为诈骗罪“被害人”并判决向其“退赔”,在法理上完全错位。如存在不当得利,依法也应返还给财产所有者(村集体),而非支付者(侵权方)。
四、司法公正之殇:超越个案的警示
贾秀华、武国光案绝非孤例,它尖锐地暴露出基层司法生态中一些令人忧思的病灶:
司法地方化与权力干预:当地方权力(特别是被举报对象)能轻易干预司法进程,将刑事诉讼异化为打击报复工具时,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便沦为泡影。纪委移送函的“乾坤大挪移”、程序违法的肆无忌惮,无不显示地方性权力对司法程序的深度渗透。
重打击轻保障的思维惯性:对辩方权利(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证人出庭权、质证权)的漠视与剥夺,对公权力违法行为的纵容,反映出“重打击、轻保障”的陈旧司法观念根深蒂固。程序在此类观念下仅被视为服务于实体定罪(尤其是满足某种“需要”)的工具。
对“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简单粗暴:对于源于民事/行政纠纷,当事人行为具有维权性质的案件,司法机关未能审慎把握刑民界限,未能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动辄以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经济纠纷,模糊了维权与犯罪的界限,导致刑法被滥用。
司法专业能力与责任心的缺失:对“三资清查”政策法律意义的无视,对农村事实承包关系的否定,对评估报告关键声明的忽略,对诈骗罪构成要件的错误理解,无不暴露出一审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重大专业缺陷。当判决书对辩方提交的大量无罪证据仅以“一概不予采信”草率打发时,司法的严谨与责任心已然缺失。
公正不仅需实现,更需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贾秀华案中,程序正义的千疮百孔与实体认定的刻意扭曲,让“看得见的公正”荡然无存。此案如同一记沉重的警钟:当司法程序能轻易被权力驾驭,当法律事实可被任意裁剪,当刑法的锋芒指向正当维权者,法治的基石便已开始松动。
唯有彻底打破“权力司法”的桎梏,将每一起案件的程序正义置于阳光之下,尊重每一个法律事实的完整面貌,坚守刑法适用的最后底线,司法才能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守护神,而非恐惧的源头。贾秀华、武国光等待的不仅是一纸无罪判决,更是一个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经得起程序与历史检验的公正答案。